“梁思成之前没有梁思成”
——纪念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
《 中华读书报 》(2011年04月20日17 版)
编者按:在风雨如晦、战火纷飞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面对疾病、饥饿和死亡的威胁,梁思成先生以科学的方法重新研究和梳理中国建筑史,将中国建筑研究的学术成果介绍给全世界。他的工作为中国建筑学的发展、为中国文化史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基石和空前的可能性。今年4月20日,恰值梁思成先生诞辰110周年,本刊特邀梁思成研究专家王军和城市与区域规划专家韩涛,就梁思成先生的学术研究与历史贡献作深度探讨。
■主持:吴子桐
■嘉宾:韩 涛(Thomas Hahn,康奈尔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教授)王 军(新华社高级记者,《城记》作者)
中国建筑研究的文化自觉
吴子桐:上世纪20年代,梁思成先生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系,接受了完整严格的西方式建筑教育。但他却最终走上了中国古建筑研究和考察、创建中国建筑学体系的道路,成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样的转变?
韩涛:我认为从外面来看,这可以说是一个转变,但我并不觉得是一个真正的转变。有一些明显的推动力触发他选择中国建筑史研究为业,而不是用西方的摩天大楼去给每一个老城市创造新的轮廓。我觉得那些推动力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他父亲梁启超送给他的《营造法式》,这本书成为他研究本国官方建筑形式的灵感来源。另一方面,我觉得他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受到的教育跟他后来做的事情是一致的,而不是一种转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培养是有价值的话,我觉得那价值就在于他学到的探究建筑形式的语言、发现建筑表达的潜在原则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中就包含了历史地理的工具,让他能够探究这些建筑形式(它们的脆弱性、地点和稳定性)在时间长河中的发展与语法。他回到中国后,这些工具也一直指导着他。第三个我觉得他是有点儿愤怒吧。20年代末的时候,西方学者研究全球建筑史,但是偏重罗马、希腊等西方建筑,也有一些懂东方建筑史的专家作了研究,梁思成读过这些研究,他觉得不合适,因此要通过研究来对抗这种西式浪潮。第四是乐嘉藻1933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这是国内最早的中国建筑史相关的书。和其他当时的西方建筑学著作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一样,这本书存在大量的简单化和错误解读。书在国内出版后,批评很多,这些都说明需要一个人来写一本正确的建筑史。梁思成也不喜欢乐嘉藻的这本书,他觉得有必要拨乱反正,并且他受到足够的训练,有能力做这件事。因此当这个领域向他敞开的时候,他被推向了这个专业的开路人的角色。
王军:我也认为他不是转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也涉及到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问题,即中国古代的建筑师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把他们当成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很高;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他们都是工匠,一般文人看不起他们。但是这些人负责中国那么多城市、房屋的建筑,这些技术很多都是口口相传。刚刚韩先生说到《营造法式》这本书,这本书的发现者、营造学社的创办人朱启钤拿这本书给梁启超看,梁启超看不懂。这里面的很多术语如耍头、斗拱等,都是中国字,但是中国的大文豪看不懂。你可以想象,中国传统社会认定的学术和技术完全是两个世界。随着中国进入现代,和西方世界接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提出来了。那时林徽因先到伦敦去读中学,她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建筑师,她一看有这样的技术,就觉得很好奇,回来就和梁思成讲。梁思成当时喜欢画画,搞雕塑、搞美术,所以他们就到美国去学建筑。学的时候正好赶上《营造法式》被发现,梁启超又看不懂,希望他和林徽因能看懂。再就是他们发现没有一部像样的中国建筑史,东西方都没有,再加上西方的建筑史都不把中国的建筑当回事,像《弗莱彻建筑史》把中国建筑摆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梁思成就觉得这个事得有人去做,他的决心很大,他读完硕士去哈佛读博士,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宫室史》,实际上他的博士论文也没法在美国完成,他在哈佛的时候倒是把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喜仁龙(Osvald Siren)等西方学者,还有关野贞等日本学者的著作都看了,发现了些问题,他就回国作调查。我觉得这是那个时期他作为中国学者自然而然的选择,确实那个领域没人做,我相信那时候如果已经有非常好的研究,梁思成之前已经有梁思成(韩:梁思成之前没有梁思成),他就不一定会去做,是大的环境促使他去做。
吴子桐:我看过资料,梁先生当时也说,如果他去做建筑事务所的话,也能做得很好。
王军:对。要知道建筑师是非常赚钱的行业,像那时候梁思成的师兄杨廷宝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他一回来到处都是活儿,他几乎成了张学良的御用建筑师,东北的很多东西都是他做的。然后又赶上1928年,国民党北伐后定都南京,中国迎来了10年的黄金期——1928年到1937年,是二战前的和平期。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和现在一样,西方大萧条,建筑师没有活儿,都跑到中国来。那时候有南京首都计划、大上海计划。杨廷宝就是在那时做了大量标志性建筑,而在建筑师有机会去设计自己作品的时候,梁思成和林徽因去做这样基础性的工作,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他们边做边整理出那本很重要的关于古建筑细部的参考书《建筑设计参考图集》,他们是抱着可以为现在服务的想法。他们也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作品,最重要的作品是北大女生宿舍和北大地质馆,那是中国最早的现代主义建筑。现代主义20世纪在欧洲开始兴起,他和林徽因在1934年、1935年设计了这两个作品,我觉得确实非常难得。
吴子桐: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梁思成和营造学社的同仁,从河北到山西,再随着战争流亡到西南,在艰苦的跋涉和颠沛流离中取得了古建筑勘测、考察和保护的丰硕成果,请谈谈梁思成先生和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考察的贡献及意义。
韩涛:我认为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对中国古建筑研究的贡献怎样评价都不过分。通过《营造学社汇刊》这个媒介,梁思成和他的同事能够记录下他们的系统研究,为50年之后中国加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打下基础。那时候是中国第一次有科学性的调查,把测绘——高度、宽度、深度都勘探、记录下来,用手绘把小的细节、周围的东西也记下来,还要拍照片。作为古建筑原型的调查与发掘者,梁思成和他的同事们定义了一个双螺旋的时间线。第一个螺旋线客观地确认古迹或遗址是什么时候建的,比如河南北部一个明朝的宗祠。而第二条时间线是关于考察者自身,通过去到那里、做测量、绘草图,可以说他建立了一条更关键的时间线:此前与此后的时间。他的存在定义了建筑处于特定状态的精确时间,若干年之后,比如他之后50年,有人来到这里,他看到的状况肯定不一样了,于是又开始了一个历史,这个历史记下了。这个时间线与客观即时的那条时间线并列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周期的历史。比如梁1932年4月到独乐寺,我后来和王军去,看到的和他看的不一样。这两个合在一起看,就很完整,给我们一些信息,1932年4月留下的信息,这些是很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梁思成、社会和学术刊物共同创造了一个公共的焦点论坛,使国内、国际的多样的群体共同关注传统古建。
王军:梁思成在营造学社的工作是1931年开始的,从1931年到1937年,是他最好的时间,那么短的时间,他和营造学社的同仁如刘敦桢等跑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对2000多个古建筑作调查。梁思成还写文章提到要有文化上的自觉,那时候有这个意识很不容易。他的背景是个五四青年,是个爱国的狂热分子。有些人爱国是觉得自己是天朝上国,后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一下觉得自己不行了,而且认为文化也不行了。但是文化哪里不行呢?从来没有对历史、文化很好地整理、总结。旧学对这些是忽视的,那会儿胡适他们提出要整理国故,一个民族要形成真正的复兴,要对自己的过去有个扎实的整理、研究。梁思成就是要通过对历史作科学的研究来实现文化上的自觉,这也是个很大的贡献。
吴子桐:我看到一些建筑学家的评价说,梁先生贡献很大,但是考察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王军:他们觉得梁思成的研究没有太重视民居,我觉得这有点求全责备。梁思成那时候面对的主要任务是把《营造法式》这本书给读懂,而《营造法式》这本书是官式建筑,民居他也零星研究了一些,但核心任务是把那本书读懂,这就要找到官式建筑实物。当时西方觉得中国的建筑不叫建筑,梁思成就是要用西方的结构理性主义的建筑理论来证明,中国建筑结构上是多么完善,比如独乐寺每个梁的高宽比是多少,现在看也是结构上最好的做法,这是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我觉得这些学者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但是他们不太了解梁思成当时的心情,他是要证明中国建筑的价值。至于南北,那时中国到处打仗,他主要精力必然在北方。一是他人在北方,二是日本打到了长城一线,华北马上就要沦陷。从梁思成在正定写的调查报告能看出,他心都是慌的,一边调查一边想着北平很快就要被枪炮摧毁,所以他是这样一种心情。我的《城记》日文版发行的时候日本东京大学举办了学术研讨会,有个日本学者就说梁思成太不容易了,梁思成做的事是我们日本几代人做的:办教育、古建筑调查、现代主义建筑设计、城市规划、文物保护。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就开始做了,至少经历了三代人。中国向西方学习本身就比较晚,又遇到了战争,梁思成已经做得很棒了,如果他还有什么没做,我们接着去做就是了。
“他把结果实的工作留给了别人”
吴子桐:1928年,梁思成出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在课程设置上,东西营造方法并重;1946年,梁思成创建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清华大学营建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中有颇多创建。请谈谈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学教育中西融合方面所作的独特贡献。
韩涛:我认为设计一个新的制度、新的课程是巨大的挑战。受保罗•克瑞(Paul Cret)的影响,那时候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建筑学院非常注重训练学生研究建筑史,同时徒手画的能力也非常重要,即将建筑师的视觉想象呈现在纸面上,这也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很重视的。你有一个想法、概念,要能把它画下来,再由工匠做出来。这是两个西方建筑培养中很重要的工作。公平地说,梁思成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卓越,因此他当然会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他清华的学生,这是他很重要的遗产和贡献。
王军:他的课程设计里有一点值得提出来,他开设了两门课: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在中国大学里他们应该是最早开这两门课的,一般人都是直接照搬教西方的建筑史或艺术史,那时西方也是主流。但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那时就开始萌芽了,他边教书边在沈阳作调查,他们在中国建筑教育里开这样的课,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46年创建清华建筑系的时候,他其实面临人生抉择,他的古建调查可以继续深入、推进,但那时候又需要建设人才,他只好把老本行放下去搞教育。那时他的课程除了建筑史等建筑课程,还开设了城市规划、社会学、市政学等课程。梁思成还是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和当时西方的现代主义大师都有交往,对美国的建筑教育也作了考察,回来之后,还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抽象图案等课程,引入现代主义建筑教育。他觉得中国古建筑和现代主义是相通的——框架结构、开间灵活、用模数法快速施工等,又希望发展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所以他很重视这一块。他的办学理念非常好,给本科生也开中国建筑史,比现在的课程设计还全面深入,现在都把学生教成工程师了。非常遗憾的是,他放下老本行去办学,而他的人文与理工相结合的办学理念后来在院系调整的时候被抛弃了。
吴子桐: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夏南悉曾评价梁思成先生“让整个民族意识到通过建筑去了解自己的历史”,梁先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写就了《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以及英文版《图像中国建筑史》。最后一本书的文稿在20世纪40年代暂存在费正清夫妇处,改革开放之后,梁思成的遗孀林洙女士和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几经周折,终于将其整理出版,获得美国出版联合会颁发的“专业暨学术书籍金奖”。请问二位如何评价这几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韩涛:《图像中国建筑史》是基于多年研究和一丝不苟的调查而成的里程碑式作品。它记录了与众不同的中国官方和宗教建筑的经典式样,相关的文本注释简洁明晰。在这本书里他回答了很多领域的问题,这意味着各个领域的读者都能够理解并运用其中的知识。我相信这本书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是因为它有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也因为它将一个如此复杂且宏大的主题清晰呈现于不同的兴趣群体面前。费正清自己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如此著名——他的通俗著作使中国对大部分读者来说都是可接近、可阅读的。可惜的是这些书都出版得太晚了,尤其是《图像中国建筑史》,1947年写成,1984年才出版。
王军:他的书都是一系列精神活动的结果,也都非常准确记录了他的行迹,但很遗憾,这几本书的出版都在他死后。想想他这辈子能够安安静静作研究的时间多么有限,作为一个学者,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通过第一手调查研究,写出那几本里程碑式的著作,确实是太不容易了。
吴子桐:他做了很多开垦的工作,把结果实的工作留给了别人。
王军:这三本书真是作为中国学术研究最基础性的工作,是给了我们第一个台阶,否则后面的台阶上不去。现在看来,任何学科的学术进步都有个瓶颈,就是对该领域历史研究的忽视。这些做得不够,导致学科没法交流。整理历史就是给人打个桌子,可以摆上茶具喝茶,现在的学科是没有桌子,坐在一起就是摔杯子。梁先生不是用杂文的方式写历史,而是最诚实地去调查、测绘,而这些成果都是可以讨论的,证实和证伪都是对学科的贡献。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为整个学科的发展、包括中国文化史的认识提供了一种空前的可能性。
梁思成的遗产:“梁陈方案”和“民族形式”
吴子桐: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陈占祥先生共同提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也就是 “梁陈方案”。这一方案由于种种原因当时并未被接纳。而如今这一方案的科学性和先见性已被证明。当年梁思成在病床上曾预言:“这个城市还没有长大,现在只会得一些伤风感冒的小毛病,但我已经看出,他将来会心肌梗塞,得高血压。”请二位谈谈“梁陈方案”对北京城规划中最有价值的是哪些?
韩涛: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方面是如何定位并分布首都未来多种多样的功能区——围绕这个问题的磋商有四个争论空间。首先是意识形态争论,这个争论空间梁思成没太参与。二是技术方面的争论,他也比较弱势。即使他和陈占祥都是多个领域的专家,但他们不是工程师。北京重建最需要的工程师,处理排水、能源、交通规划、住宅建设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问题,像北京直到1957年才开始真正建设科学的排水系统,而梁思成完全在这些领域之外。三是1949年开始苏联专家来到中国,这些专家的教育、培养有意识形态背景,和梁思成不一样。海外专家更有话语权,而且苏联专家大部分从莫斯科来,他们从1945年开始做这些事情,经验丰富,对中国来说帮助快些。四是行政—政治的争论空间,梁思成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北京是要建全球社会主义首都,要超越莫斯科,把全球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起来。梁思成没有之前的基础,因此他的影响力就非常受限。这四个争论空间是最主要的,梁思成就逐渐被边缘化了。
第二个方面是分析规划本身,即在五棵松地区建新区新城,主要是将政治功能区放在那里。这不是第一次新老城区的冲突,第一次是1929年国民政府的首都计划,请墨菲建筑事务所做的。他们的设计原则和后来的“梁陈方案”很像,都是将政治功能区移出旧城,为之建立一个轴向的、几何上均衡的建筑群,但墨菲的方案一直也没有实现。据我所知,“梁陈方案”是第一个以在原址附近复制新城的方式将北京从它自身的急速扩张压力下解救出来的方案。规划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在于他找的位置,一是引起了关于日本的不好回忆(1938年,为了容纳日益增多的日本人,要在五棵松地区建立新的聚居区,并且这一计划部分地实现了),一是离北京太远,交通那时还不便。这两个因素加上前述的四个争论空间,他的位置就被边缘化,最终失败了。“梁陈方案”是有益的,但是他们从一开始就受到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因素的限制。
另外,如果要实现梁思成的规划,我认为需要六个条件。一是把所有空间区域功能化,即按照功能来划分区域。二是北京要延缓工业化,甚至完全不要工业化,一个工厂都不要盖。三是隔离整个城市,在收集到对城市实施最小限度破坏的足够数据之前,中止一切新的建设和破坏。四是为了临近区域的规划与复位,进行大规模暂时性的居民搬迁。五是为了配合更新与复位的项目,要针对土地拥有者和土地使用权制定相应的法律——也就是说,不论城市乡村、有无宗教信仰,所有人都要被征收土地、重新分配。六是在讨论城市与大型社会的未来时,必须建设共享与参与型的基础设施,这即使在西方也是个难题。
很难讲“梁陈方案”如果实现了会怎样,而在我看来北京的发展最值得批判的是,在内部解决一切基本需要的“单位制”取消之后,需要给每一个个体提供一贯的、有效的、扩张的市政服务。
王军:我是个北京市民,城市规划的方案对我的生活产生了影响,比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这和北京失去一个合理的城市结构有关。我觉得“梁陈方案”对北京比较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它的一个核心思想是要平衡地发展城市,就是说大型城市不能采用单中心结构。把老城拆除建新城,就导致大量工作机会集中在中心区,而中心区已经有密集的居住人口,人还得搬出去,导致人们在中心区上班、在郊区睡觉。梁思成说如果以后交通出现大的问题,这次选择就是祸根,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城市规划最基本的思想。一般人觉得他是出于保护古建筑的考量,这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我觉得如果在一块没有古建筑的空地上建城市,特别是一个大型城市,单中心的结构也是最糟糕的。他是要推进居住、就业的基本平衡,希望形成平衡的多中心的城市结构。北京现在人口近两千万了,居然是个单中心结构,这很要命,大拥堵都与此有关系。现在虽然搞地铁、搞公共交通,但结构问题不解决,大规模的跨区域交通被制造出来了,再怎么用公共交通来解决,仍然有太多人痛苦地拥堵在公共交通里面。
吴子桐:梁先生先生曾经讲过,“如果世界上艺术精华,没有客观价值标准来保护,恐怕十之八九均会被后人在权势易主之时,或趣味改向之时,毁损无余。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建筑的“民族形式”曾经是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近年来的建筑似乎已经失去了“民族形式”,比如北京,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建筑师的试验场。请问二位对此有何看法?
王军:我认为梁思成对民族形式的观点是他对中国古建筑发现、整理之后的理解。现代主义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他在美国学到的是学院派的理论,但是他回来后马上就注意到了现代主义,马上做出中国最早的现代主义作品——北大女生楼、地质馆。他认为中国古建筑和现代主义是相通的,都是用框架、梁架承重,能够进行大规模的预制、安装,用模数法来做。中国人不做假东西,像斗拱,都是外露的结构,只是到晚期才变成装饰了。像屋顶的曲折,也都有结构的考虑,比如让瓦片咬得紧点、让房子更能适应日晒雨淋等——因为功能而产生形式,而形式是美的,这些和现代主义是相通的。所以,梁思成相信能够做出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来。这个命题是面向未来的,也是需要现代人来回答的。
韩涛:建筑环境所表达的文化自觉与真实性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只中国的城市遇到。城市的民族形式可以用多种方法呈现:完整综合、相对稳定的城市环境(比如现在几乎消失的北京胡同或上海里弄),对传奇过去的可控制的、阶段性的展示(比如世界上许多旅游城市),由法律保障的对城市建筑形式的永久保存,还有任何介于这些之间的形式。但我是往前看的,也就是把民族形式放在全球化的视野里来看,我认为民族形式基本上是不需要的。在一个市场驱动的多元世界里,全球的共同体正在形成一致性。完全的价值观一致不再是增长的必要路径,适应性的、积极主动的规划才能照顾到新的多元主义,并为新的认同、新的知识与新的行动领域(比如生态城、生态村)提供基础。这些规划有望超越本土的、区域的和民族的界限,也就是说这样的建筑语言遵循的法则不再需要依附于一套规范、一种美学标准。在效率与竞争的要求下,民族形式将不是必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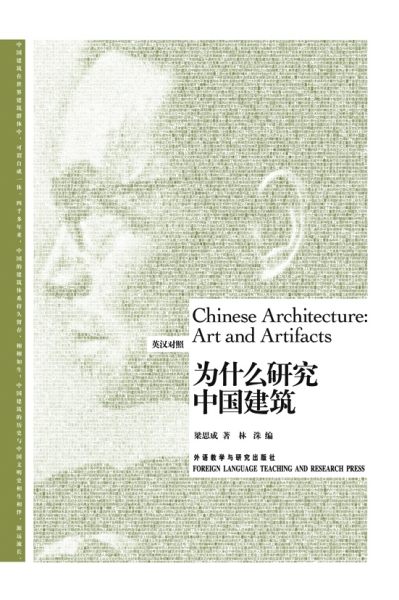
《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英汉对照)梁思成著林洙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4月第一版定价66.00元
0
推荐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